年 味 年 俗
崔建明
马上要进入腊月啦,想起了很多有关过年的记忆。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它起源于岁首祈年祭祀的仪式。早在上古时代,人们会在一年农事结束后新一年开端的时候举行祭祀,遥敬天地众神,感念祖先恩德,企盼来年丰收平安,慢慢地就形成了“过年”的风俗。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不再以祭祀为最重要的内容,但保留了各种迎禧祈福的新年习俗。
进入腊月,东台人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首先是腌制咸货。一般人家会腌上几斤咸肉,两条青鱼,再灌几斤香肠。家境殷实考究一点的人家还会腌制猪头、风鸡、野兔等。腊月里从每户人家屋檐下挂的咸货多寡、品种繁简,主人的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并可见一斑。
腊月里还有一个年货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必须弄的,那就是戡月粉划糕。东台人为什么把做年糕称之为“划糕”,我不得其解。划糕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首先要把糯米淘净沥干,然后找划糕的加工点排号,有时不巧轮到你家夜里也要去帮着洗笼布、拾糕。我家最远曾跑到西溪去划糕,隆冬腊月滴水成冰,有时还会遇上雨雪天气,但忙年的喜悦让大人和孩子劲头十足。听我妻子说,她小时候最喜欢吃刚出笼的糕,说是很糯很香,可惜我没有吃过。年糕划好后要放在水桶里盖上干净的纱布捂上两天,这样年糕吃起来口感更加软糯瓷实。东台人有多种年糕的吃法,最简单的是用开水烫或放在粥里煮,沾糖吃;讲究一点的煎糕,分成甜咸两种口味,先用菜油煎成表面焦黄,吃咸的话则用自家泡制的淡黄色的豆色酱油一烹,撒上翠绿的蒜花,品相极佳,口感鲜香;甜的浇上糖水即可,年糕的表面糊上一层晶莹的糖稀煞是诱人。
在腊月前更早的时候,母亲会张罗为我们准备过新年的衣服和棉鞋。春节前裁缝店和上鞋子的生意红火的很,衣料和鞋料送晚了可赶不上过年。那个时候工业产品不丰富,许多东西基本上是半手工制作。我们过年穿的新棉鞋都是母亲做成半成品,然后拿到鞋匠家加工,上鞋子的师傅好象都是个体经营户,家就是店,店亦是家。棉鞋的样式有两种,一种是俗称“河歪扇”(两片鞋邦如河蚌壳形状);还有一种讲究的是系鞋带的,比较洋气,但面料似乎都是黑色灯芯绒。
如果说春节前纷繁的准备工作是“九层之台”的话,那前面说的这些只是“起于累土”。计划经济物资匮乏的年代,凭米本子(购粮证)可领取各类票券,有烟票、肉票、粉丝票、鱼票,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为了让老百姓有钱购买这些平时生活没有的年货,每个单位都会预支下月的工资。人们手头宽裕了,兴奋的拿着五颜六色的票券到食品公司、糖烟酒公司、蔬菜公司以及粮店去排队采办年货。如今你把这些往事告诉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好笑。
春节前打扫除也是一件极其重要同时也是很辛苦的事。东台人的风俗是进入“大寒”节气后就可以打扫除了。听我母亲说,“大寒的太岁不管闲事”,所以扫帚随便哪都可以扫,无所顾忌,东台人称之为“掸尘”。做的认真不认真,打扫的彻底与否就看主人的讲究程度和房屋的优劣了。我有一位同学的妈妈讲究到用抹布把屋梁上的椽子都擦得干干净净。房子打扫干净了,要考虑贴几张年画,增添喜庆的年味。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春联年画都在新华书店,大多是八个样板戏的剧照。我们家的年画春联每年都是父亲单位赠送,其中必有一张粉红色的慰问信,因为家父建国前参加革命当过兵,属于“六种人”。年画年年新,春联几乎没变过,上联“发扬革命传统”,下联“争取更大光荣”。我们上学得的“五好战士”奖状(相当于现在的三好生)也是装点春节的一道小风景。“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过去人们家里的日历是一个彩印的纸板订上一本日历挂在墙上,过一天撕去一张,到年底连纸板一起换新的。有一年也不知母亲是忘记了还是为了节约,只买了日历没有买纸板,新日历配上旧纸板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没有新年的气象,临机一动,我用一张白纸糊在旧纸板上,涂上淡蓝色,然后画了一株红梅,订上新日历,咦!还满象那么一回事,跟新买的似的,母亲连着向邻居夸耀了几天。随着年龄的长大,过年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写春联写福字,之所以能写一手勉强可以示人的毛笔字完全得益于幼时母亲的教导。母亲说,字是人的大褂子,人家不知道你的学识如何,但一看你的字不丑,就会认为你有点文化而不致小瞧了你。记得我第一次写的春联据说是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副春联,是五代后蜀主孟昶刻在寢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邻居中有位中学老师看到后不吝褒奖一番。有一年我去上海做腿部手术,没有回家过年,母亲把我去年写的福字用剪刀细心剪下,然后贴在同样大小的红纸上,跟邻居开玩笑说是她写的,人家说,老太太还写的不丑呢!
腊月里,街头巷弄会突然冒出代客加工包子的地方,一个大铁桶改成的炉子内吐着红红的火苗,笼上冒着热气腾腾的白雾,那就是一活广告,告诉人们,过年啦!加工包子啦!主妇们在家中备好馅芯,青菜猪肉蛋皮木耳炒的包菜包子,豆沙白糖猪油的包糖包子。主人洗笼布,拾包子,忙得不亦乐乎,看见邻里熟人还会递上一两只刚出笼的包子硬要给你尝尝。
听老人讲古,旧时东台城稍有规模的酒楼茶肆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都要摆酒设宴。一来大伙辛劳一年了,犒劳一番,二来即将进入全年生意最红火的旺季,老板要拜托伙计们实心卖力也好赚个盆满钵溢。而这一天烧火的师傅必定会被老板请到东台人称为“上岗子”的首席就座。大师傅炒的菜除了手艺外全靠火侯,该大火的时候给你来个不温不火岂不急煞人?所以烧火师傅坐“上岗子”既有慰劳之情亦含拜托之意。另外,假如哪个伙计也被请到“上岗子”入席,估计这顿酒席他是无论如何也吃不出滋味。因为他这一年干的不好或不够机灵,吃完了饭老板会上他卷铺盖走人。细细揣摩,这其中蕴含着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凡事讲个仁,辞退人家不直接讲,委婉含蓄,礼仪周全,请伙计多多包涵,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好聚好散,但愿日后再相逢。
旧社会时期的大商铺到了大年三十的上午就早早的上闼板歇业,说是为了让那些提篮挎筐引车卖浆的小商小贩做点生意,此举名曰“让市”。其实大的商铺除去自家店堂的零售外,大多经营批发业务,街头巷尾摆摊设点的小贩们的货,大都从他们那儿进,有的甚至是赊欠的。小贩们能把货卖出去既可回笼资金,又能扩大批发业务,理顺了销售渠道,大老板们可谓精明到家啦!
腊月二十四以后,年味越来越浓了。到处是忙碌的人们,每个人都迈着匆匆的步伐,脸上溢满笑容。那些家庭主妇们也少了往日的修饰和清爽倒显得蓬头拉呱了。阳光下,巷子旁院子内空场处挂满了浆洗干净的床单被褥,还有用筛子晾晒的月粉、糕饼。小孩在其间穿梭㛸闹,清脆稚嫰的笑声不时响起。大街上更是人声鼎沸,熙来攘往,旧城的街道只有七里长街,平时市民们基本都是步行,别说汽车连自行车也很稀少,碎石铺就的街道通行顺畅。可到年底,四乡八镇以及附近兴化的农民进城采办年货,宁静的台城立马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记得当年东台街上放映越剧《红楼梦》电影,恰逢农民进城买卖山芋藤,人车塞满了整个街道。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开会的时候说,红楼梦,山芋藤,东台街上人挤人。人多难免交通堵塞,最容易造成“塞裆”的有三个地方:新坝人民饭店门口,工人文化宫向西的细长小街,还有就是北关桥。北关桥下河道两岸泊满了木船,水泥船和挂桨船,辛劳了一年的农民拉家携口,乡邻结伴你呼他喊的进城逮小猪,办年货。装扮那些青年妇女最光鲜的要数她们头上围裹着的红的绿的紫的花格子的三角巾,酱红色的脸庞上露出几小块冻疮的斑痕,丰收的喜悦和进城的欢欣让她们脸上挂满了笑靥。曾经的北关桥是东台城人气最旺的码头,桥北是工业区,到了中午工厂的工人下班,工人兄弟和农民伯伯在北关桥来了个大会师,人挤人,箩碰筐,你不让我,我不让他,整个北关桥堵个水泄不通!我曾有一次被堵在北关桥上一个多小时,前不得进后不可退。后来消防队来了几十个战士硬是在桥中间纵向拉起了一道人墙,分左右通行方才慢慢的疏通了。
春节前热闹繁忙的地方,还有理发店和澡堂子,相比而言,澡堂子更加拥挤。旧城改造前浴室并不多,新桥西炕坊旁有一家,西十字街有个清一池,人民剧场斜对面是曲江浴室,大会堂对面巷子里还有班东台浴室,零零星星的工厂也配有职工浴室。平时尚可满足需求,但春节前台城周边乡下的农民都要进城洗个澡,那可就人满为患了。上面更衣的地方一座难求,遇见熟人朋友跑堂的可以帮着把衣服打个卷用长长的杈杆挂起来,待你洗好澡也许就给你安排好座位了。忙不迭的冲进浴池内,一股混杂着汗臭的难闻气味扑鼻而来,不大的池子内象下饺似的人挤人,屁股挨着屁股,哪是洗澡啊,如同打仗。池子里的水混浊如泥汤,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争先恐后的挤进泥汤中而全然不顾干净污浊与否。正常情况下,男浴室客人澡后是有热手巾把子擦身子的,春节前这项服务就免了。小时候跟父亲去洗澡,跑堂的对我父亲加一恭维,专门用脸盆打了干净热水,挤个热毛巾递过来。父亲接过毛巾帮我擦了起来,跑堂的一愣,“你格小伙啊?”连忙又递来一条热毛巾,当然啦,来而无往非礼也,父亲掏出大前门香烟,跑堂的自己抽出一支夹在耳朵上,父亲的手轻轻地抖了抖,跑堂的复又抽出一支叼在嘴角并不忘及时为家父点上火。那一瞬间我对父亲多了一份崇拜!

随着春节到来的脚步,巷弄内会弥漫着一股特别诱人的香味。那是煎肉元的味道。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桌上如果少了烧肉元似乎低了一个档次。东台人喜欢用金针菜烧肉元,但金针菜在过去是要用批条买的。没有金针菜就退而求其次,用黄芽菜、百合头小青菜也蛮好。家母好象多年以来一直执著的坚持用金针菜烧肉元。噢!原来计划经济年代父亲的工作单位经营土特产日杂果品。除了备下荤腥菜外,好多人家还会炒上满满一大盆“干蔬菜”,这里的“干”字东台人读成“锅”字音。用早早晒干的胡萝卜丝配上百页咸菜等一起炒,最后撒上大蒜花即可,没有汤汁故为“干蔬菜”,这是春节前后喝粥的佐菜,平时都是咸菜萝卜干,我想过年啦,讲究一点。
大人花钱劳心劳神操办过年,小孩子却盼着过年。我小时候常常会躺在被窝里掰着手指算还有几天过年,把所有能想到的零食数了个遍,企盼着这些想象变成真的,相反对家里准备什么过年的菜不太注意。过去东台镇机关大门西侧有一片临街的空地,背阴向阳,平坦宽广,春节前是炒花生炸炒米的好地方。帮人家炒花生瓜子的中年妇女就住在马路对面矮房内,瘦高个,头发有点卷曲,平时很少看到她的笑脸。听我姑母说她解放前就开炒货店,与姑母的皮鞋店是紧邻。炸炒米的师傅虽破衣烂衫,鼻黑手乌,我觉得却颇有职业操守,每当开炉前必拖长音来一噪子“响 啊 ”提醒过往路人注意,尤其是别惊吓了老人幼童。家家户户派出干炒年货这活计的大多是半大孩子,孩子们也乐此不疲,炒花生、炒瓜子、炸蚕豆、炸山芋干,当他们拎着大包小包向父母交差的时候,从不会忘记把自己的小口袋装满。
二十七、八夜,人们的生活更加纷乱忙碌,连一日三餐的规律也基本打乱了。大人小孩肚子饿了随便弄点对付一下就行了,孩子们更加期盼三十晚上那顿丰盛的年夜饭。除夕,在人们的盼望中到了。我小弟早上撕去一张日历,惊喜的叫道:妈妈!今天是除歹!母亲笑着说道:是除夕,不是除歹!
各家各户都拿出早就置办好的年货,力求丰盛的准备年夜饭。其实细想想,节前所有的采买辛劳都为了三十晚上的团圆饭。尽管各家各户的菜不尽相同,但有几样菜肴好象是与年俗有关。旧时为官做生意的人家,三十晚上必定会用猪肝猪大肠一起炒,东台方言土语称猪肝叫“猪官”,这道菜寓意“官大长”;烧两条鲢鱼从三十晚上摆到大年初五财神日子才能吃,表示“年年有余”;还要烧一个青菜豆腐汤,青菜豆腐保平安。也有人家烧芋头阿羹汤,吃了芋头遇好人。家父和我喜食芋头,所以我们家选择后者。不管你家烧什么汤,三十晚上吃饭是不能泡汤的,以免出远门碰上雨雪天气。
大年初一早上当我们醒来后会发现枕头边有一双新袜子和崭新的两张一角钱,至今还记得上面有好多人扛着铁锹推着小车去劳动的图案。穿上新衣新鞋新袜,兜里装着两毛钱,那是什么感觉?其牛逼的程度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土豪开着桑塔纳手提大哥大!两毛钱放兜里几天后我会交还给母亲,善于持家的母亲在节前购买年货的时候总不忘预留下一笔钱用于我们开学后缴学费。兄弟姐妹好几个上学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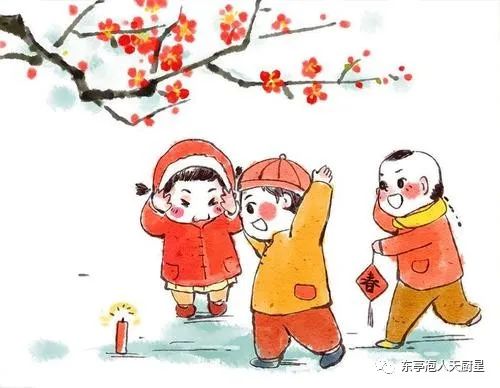
拜年是春节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拎上几包茶食给长辈拜年是小辈的礼数,街坊邻居见了面彼此说几句吉祥话也是约定俗成的乡风。十年文革期间,大年初一早上,一位在东台镇机关工作的S姓复员军人,在巷子里遇到熟人并高声且虔诚地喊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对方立即回应: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滑稽而又不可思议的场景很多年也不成忘却。
一年又一年的春节,让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步入花甲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年味似乎越来越淡了。也许你还能从火车站肩扛蛇皮袋的农民工随着拥挤的人群向前挪动的脚步以及广东肇庆冒着雪雨一路西行的二十万摩托大军那飞驰的身影,或许是高速公路上逶迤几十公里回家过年的钢铁长龙捕捉到一点春节的味道。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人们更多的选择就地过年,让原本渐淡的年味日趋平淡寻常。但“年”既然能传承千载,证明人们对年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情感。以前在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也是表达想企盼来年可以衣食无忧,生活更加美好。因为“年”是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特珠时刻。但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新衣服、压岁钱、美食这些在以前只在过年才能享受的东西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我们已不需要这种方式表达。可这份向往更加美好生活的心意还是要保留的。回家!团圆!这才是新年的意义,也是“年味”最核心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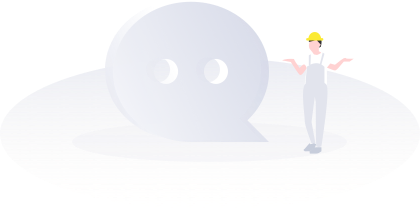
这里还没有新评论





我也是有底线的